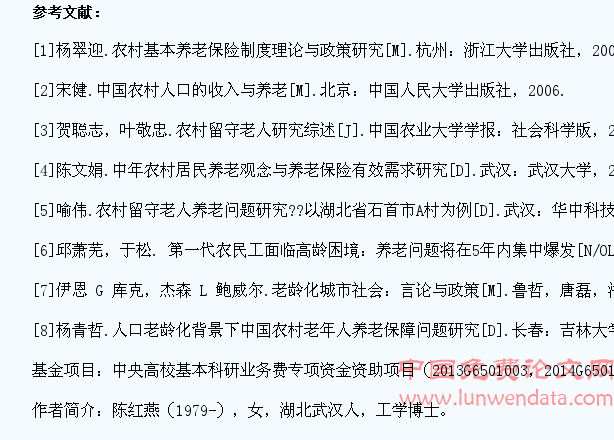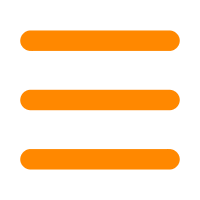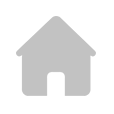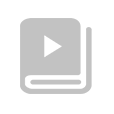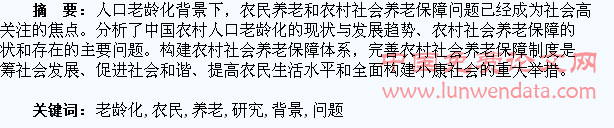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 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1-828X(2014)09-0000-01
到了现在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广受社会关注,其可能的进步形势、影响与应付之策也渐渐得到了广泛的研究[1-3]。面对老龄化的严峻形势,社会关注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养老。而这个问题在中国却又存在两个不一样的层面,一个是城市层面的,另一个是农村层面的。几十年以来特别的进步模式使中国社会面临紧急的城乡割裂,任何问题可能在农村与城市都有着完全不一样的逻辑。而恰恰,在中国特殊的进步模式之下,很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并且大多数时间在城市生活但同时却又不可以真的定居城市。这带来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导致农村社会常见成为老人社会,其二是这类未能定居城市的农民工未来的着落在哪儿。这样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农村确实较城市严峻且复杂。用更为专业一点的话来讲即中国社会人口的老龄化情况不只呈现未富先老的特征,而且还存在着紧急的城乡倒置。未富先老使社会经济进步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潜在负面影响,而城乡倒置又使这一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因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在现在的状况下对农民养老问题进行愈加深入的研究,以期在问题真的出现之前做好充足的应付筹备。
有鉴于此,本文将使用内部视角,从农村老年人口面临的养老现实困境出发,并结合老龄化未来发展趋势,对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研究将使用案例陈述的方法试图尽量全方位地展示农村老年人口养老可能遭遇的问题,因此在个案的选择上本研究不需要代表性,而是寄望于将这一问题可能的每个方面展示出来。本文只做问题的展示,并不探讨对这类问题的具体解决之策。在结构上,本文将依据农村老年人口的特征将个案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有关当下“留守老人”的案例,其二是有关第二代农民工的案例,即随年龄增大而可能成为“留守老人”的案例。同时本研究所选个案的来源并不拘泥于一时一地,而是尽量将自己调查或者公开出版物上出现的个案集合起来,如此做的目的还是如前所述尽最大可能展示老龄化背景下农民养老问题的每个层面。
1、已成为“留守老人”的农村老年人的养老
所谓留守老人,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空巢家庭的另一个称谓罢了。只不过空巢家庭这个定义的涵义更广,任何一个核心家庭在子女长大成人后只须子女长期离家也就成为了一个空巢家庭。而所谓留守老人则不过是农村空巢家庭中的老人而已,农村家庭的子女进入城市并大多数时间在城市生活而导致老人“留守”家园。假如要下个概念的话,好像可以如此来界定:长期居住在户籍所在地 、 年龄高于60周岁的农村老人,且其子女及子女配偶长期不在身边者。那样如此一个群体在养老方面会面临什么问题呢?
案例1:年近八旬的庄稼汉
张老汉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到今天已年近八十,老汉家有3个儿子。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3个儿子相继南下广东打工,其中小儿子通过努力在2005年左右终于自己翻身成为老板,在虎门自建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制鞋厂。鞋厂的收益非常不错,张老汉的另外2个儿子也舍弃了原来的工作而进入其三弟的鞋厂。但即使是在如此一个家境富裕、儿女孝顺团结的家庭中,张老汉却一直未舍弃农业生产。虽然张老汉的3个儿子曾多次劝其爸爸妈妈舍弃耕田转而到城市去与他们一块生活,但每次都遭到老汉的强烈反对。(访谈时间:2012年7月)
通过案例1的描述其实可以看到:第一是农民的养老诉求较低。从单个个案得出的结论并没代表性,事实上,陈文娟[4]曾以规范的问卷调查方法对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进行过专门调查,并指出农村居民的养老预期总体并不乐观,对养老问题的担忧较高。遗憾的是其调查主如果针对中年农民,缺少对老年农民的调查。但可以理解的是,在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中虽然养儿防老具备非常强的正当性,但日常年老一代对年轻一代的需要却绝不是不讲人情。在多地农村的调查中笔者亦察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不少农村的老人与子女分居住在低矮的“老屋”当中,其生活水准明显低于子女。但就是如此的老人,对生活的认可度并未必就低。反而,只须生活能保持正常的一般标准,做爸爸妈妈的更期望子女过得比自己好。如此,社会保障在规范设计上或许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农村老年人认可的规范低于社会认可的养老标准[5]。这样一来可能随着而来的问题便是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可度较低。笔者当然不觉得既然农民本身的养老诉求较低就应该因此而设置较低的社会保障标准,问题的重点是怎么样提升农民的养老意识。
第二,农民对作为财产的土地的认识是影响其养老观念的一个要紧方面。正是因此,即使是家境颇富的张老汉也一直不想舍弃种田。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用途早已为学界所认识,但更为要紧的是该从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有人因此而强调保持当下土地规范的重要程度,也有人强调土地的社保功能妨碍了土地正常经济功能的发挥。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农民“恋土”而不愿离开土地,无非是由于心忧离开土地后生活没着落或者说“保障”,以至于不论土地收益高低,在未寻得城市立足之前是非常难想弃土离乡的。之所以需要土地担当社会保障的功能,不过就是由于与城市里的“单位人”相反,除去土地以外非常难说还有哪些靠谱的依靠。这一点即使是国家大力推进农村医疗与社会保障的今天好像依旧这样。
事实上,以上两方面的剖析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即老年农民表面上看来是由于观念落后而出现不想参与社会养老并且对我们的养老情况也不甚在乎,其实质反映的还是他们对子女有无真的稳定生活的担心。这种观念可能看上去陈旧、守旧甚至于在不少激进的人看来是完全没必要的;但无论如何说,无法避免的一个事实却是假如不可以从规范上解决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打造稳定事业与获得稳定财产的可能性,而只是企图将适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保体系扩展到农村的话,如此的做法可能并不讨好。毕竟,从个人的角度而言生活最大的保障只在于所在家庭是不是打造在一个稳定的事业基础上。 2、马上成为“留守老人”的农民的养老
留守老人是现阶段已经进入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那样比他们更小的一辈,即现阶段年龄在50岁边缘到60岁之间的农民(学界通称的“第一代农民工”)则是可能非常快就要成为“留守老人”的一代。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国内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国内农民工总量已达25278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初次突破3600万。然而,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进步统计公报显示,国内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4140万人,占比只有16%。尽管国内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4岁,50岁上下的人好像仍未嫌老。但作为主要在工厂或工地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而言,进入50岁将来显然意味着进入了一个体力衰退的高峰时期。那样这个群体面对的又是什么呢?
案例2:超龄务工者老谢等[6]
59岁的谢国万说,64岁的老伴身子不好,去年得了一场大病还动了手术,假如在家陪老伴不去打工,就断了家的生活来源。为此,他非常纠结。谢国万是开县团凤村人,36岁开始外出打工。自2009年始,早报记者已连续5年采访了谢国万,每年新年他都在纠结“走还是留”,但在吃完元宵节的汤圆后,他最后都扛起行李,坐上了南下广州的客车。
5年来,打工所得占谢国万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达90%,若停止打工的脚步,就只剩下960元/年的养老金,1000元/年的低保,外加500元/年的土地收益(算上其爱人1000元/年的低保,两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500元),根本很难保持夫妻两个的生活。为此,年近六旬的他还是想着咬牙再赚几年100元/天的苦力薪资。 (《东方早报》2013年2月26日)
假如说对于6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而言,养老最大的障碍在于观念问题的话,那样对于这类50多岁的老农民或农民工而言则面临的困难要多得多。他们一方面面临自己事业的转折,即到底是回农村还是留城市的两难选择;其次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子女的问题可能仍远未解决。对于如此一个群体,假如连最低的“社会保障”都没(事实上大部分确实没)则显然有失社会公义,但假如说只须提升其养老标准,每一个月多发点保险金就可以解决其“保障”问题,这恐怕亦只不过天方夜谭。
面对老龄化问题,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可能存在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城市可能还真能像一些乐观的国外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城市化进步至少不会由于老年人口而面临主要资源匮乏。相反,它们非常或许会用一群活跃的或相对活跃的老年居民,可以并且将为城市社会做出广泛的贡献而非依靠于城市。”[7]相比之下,第一代农民工的工作年龄即使再往后推延5年,在自己并无稳定事业又缺少社会养老保险的状况下,要使他们在社会生活甚至于消费范围变得“活跃”或“相对活跃”怕也只能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
3、结论与讨论
对于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发展势头,杨青哲[8]在其博士论文中做过详细的估算。他以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关于农村人口的有关数据做基础,预测了将来40年(2010~2050)中国农村各时期总人口数、少年儿童人口数、劳动力年龄人口数、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依据他的估算,即使是根据最高可能的总和生育率(2.3)进行推算,农村少年儿童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在将来40年时间内将维持递减趋势,在 2025年,65岁及以上人口数超越1亿,到 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达到峰值,约为 1.5 亿。
40年乡村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从 2010 年的 10.06%上升到 2050 年的 44.18%,共增长了36.33 个百分点。这一变化趋必然然致使社会抚养比的提升,杨青哲估计到2050年总抚养比将超越1。
非常显然,紧急的老龄化会给整个社会养老体系带来沉重的重压。只有将自我养老(即依靠自己劳动收入的养老)、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方能缓解这种重压。这自然意味着要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体系的建设,推广并进步现有些新农保规范,但围绕老年人自己的劳动力再发挥及家庭养老支持在农村而言却才是具备最后决定意义的问题,由于现在新农保规范的三大资金支柱乃是个人交费、集体补助与政府补贴,在大部分农村区域集体补助所依靠的集体经济组织事实上已名存实亡,而个人交费状况也完全取决于家庭收入。而对于中国农民家庭而言,家庭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没办法积累财富,可以说这才是农民养老的死结。
因此,要加大农民的社会保障,最有力的举措还是在于持续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并且同时进行金融规范与土地规范的革新使得农民的财富可以积累起来。事实上近些年来,国家愈加看重三农问题,并试图进一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构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倡导。然而这类问题事实上都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较为全方位的解决,同时即使农民收入得以增加,但假如仍没办法达成财富的积累,那样老龄化趋势下的养老问题仍将没办法解决。